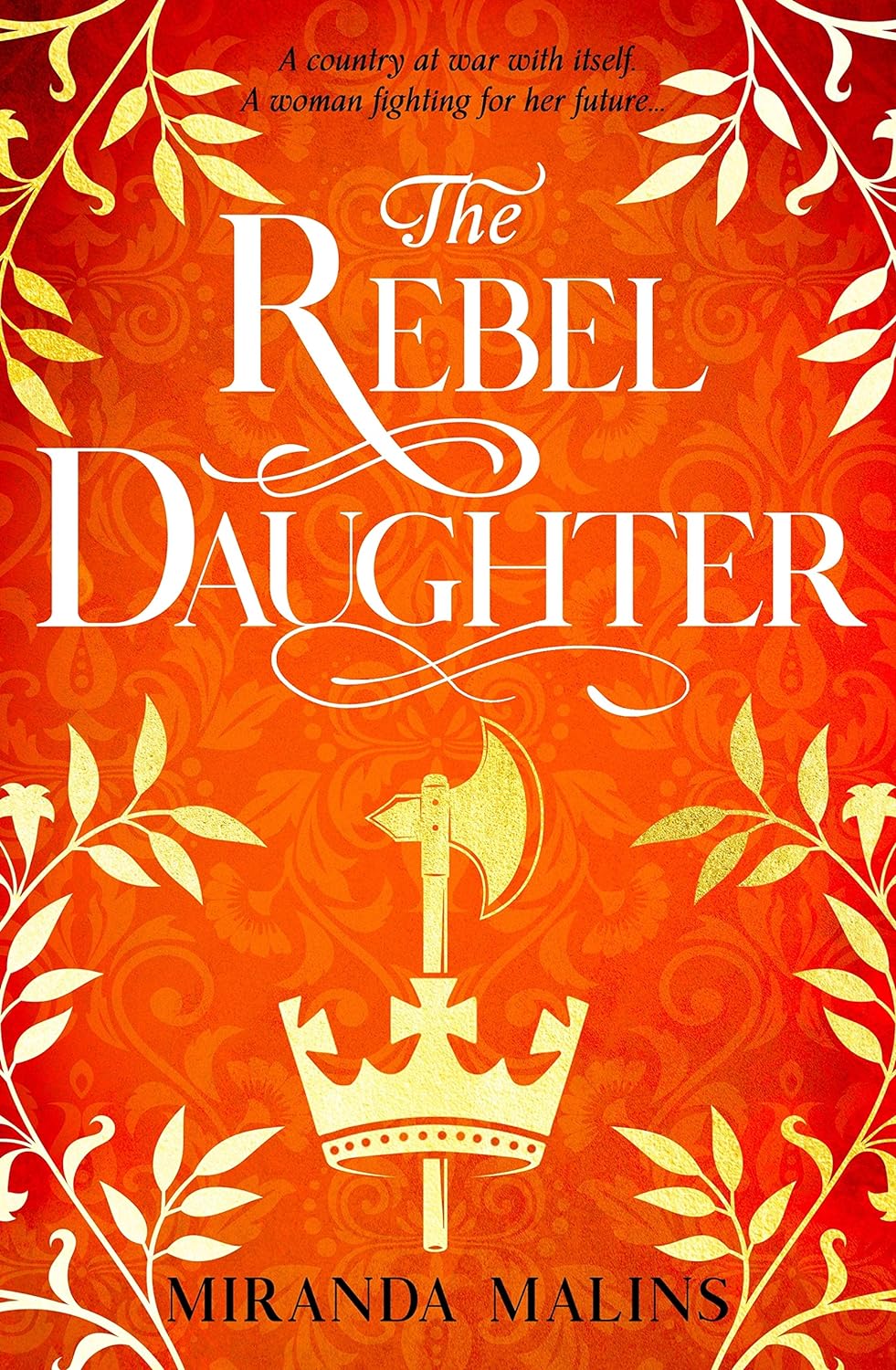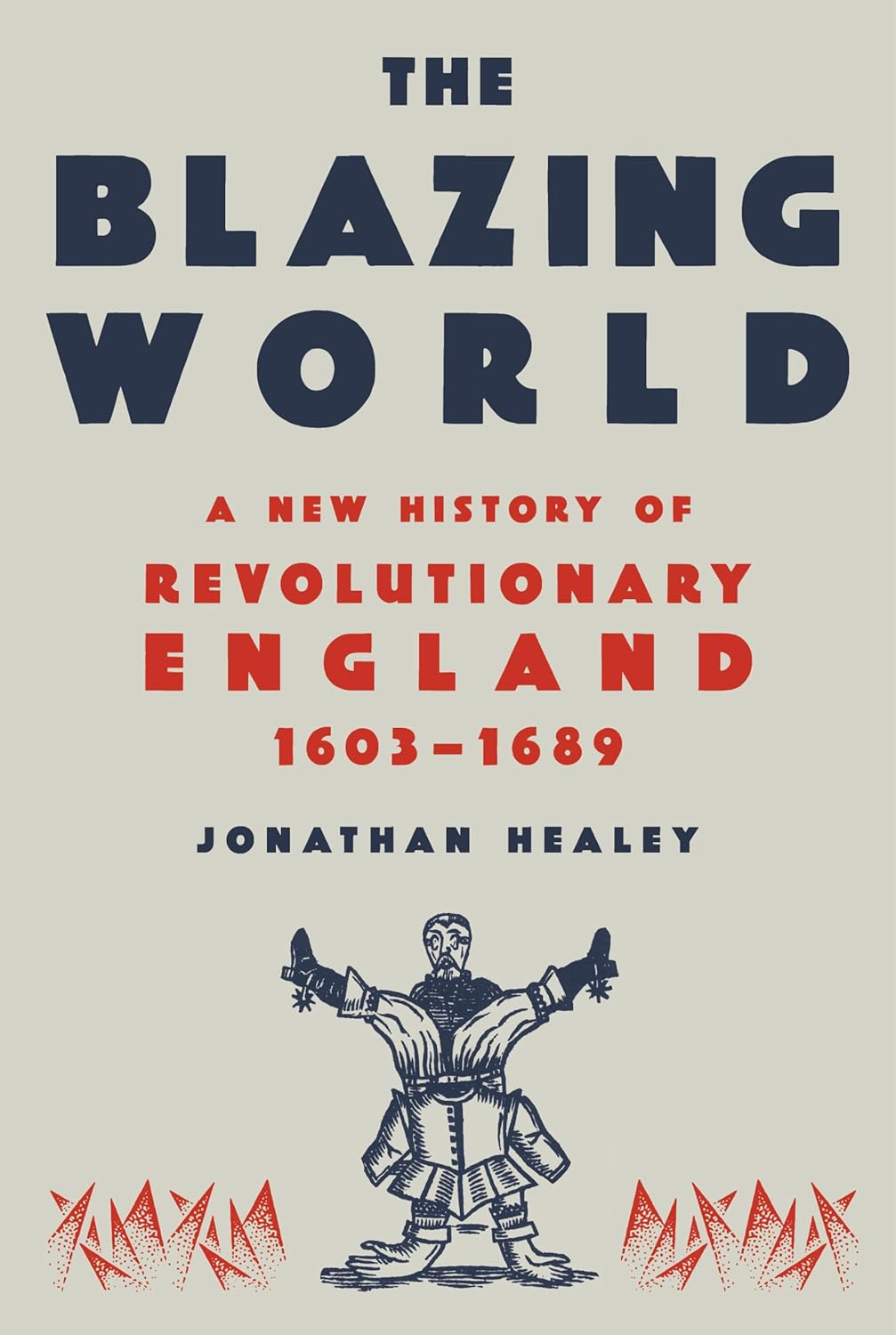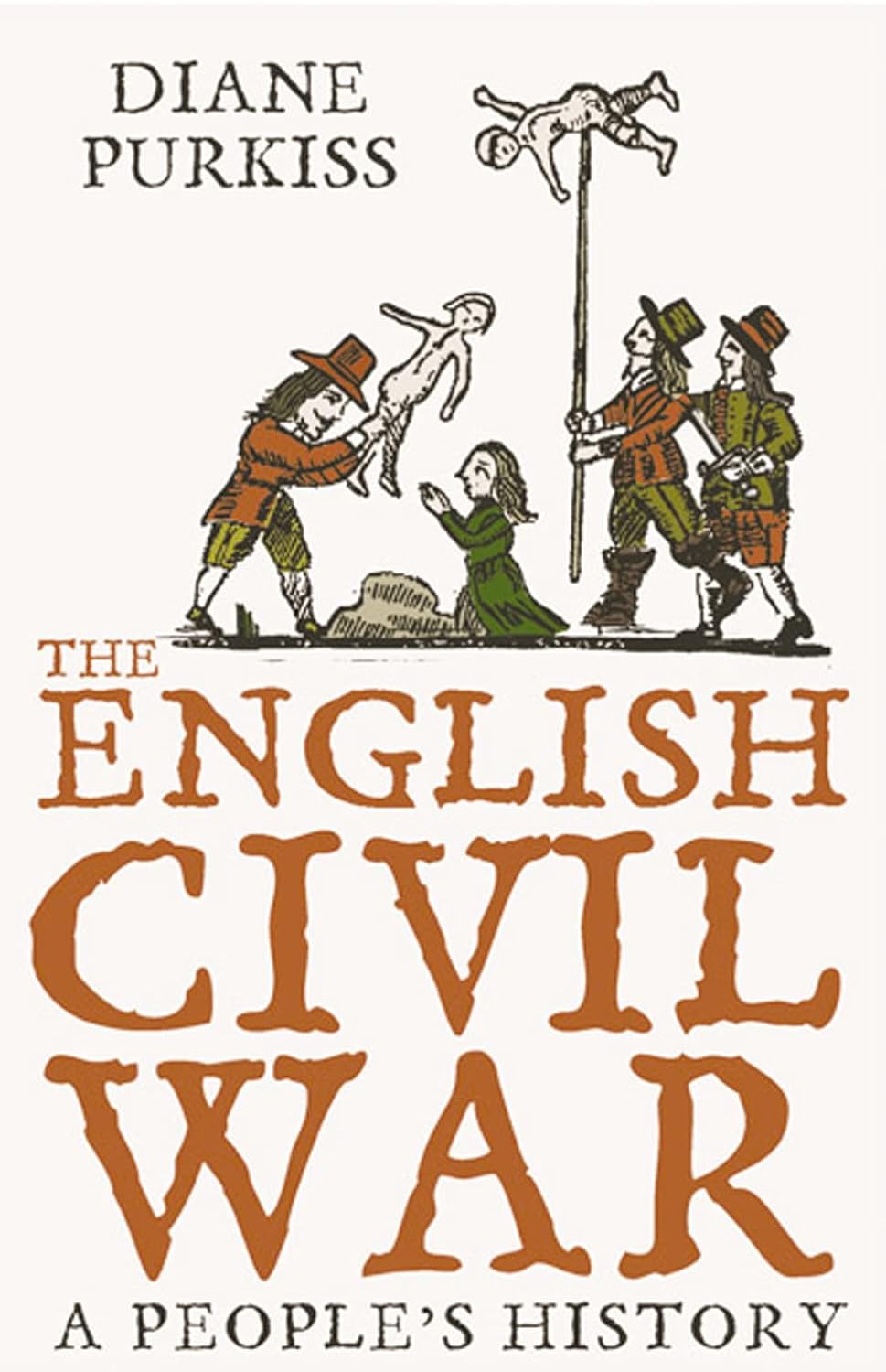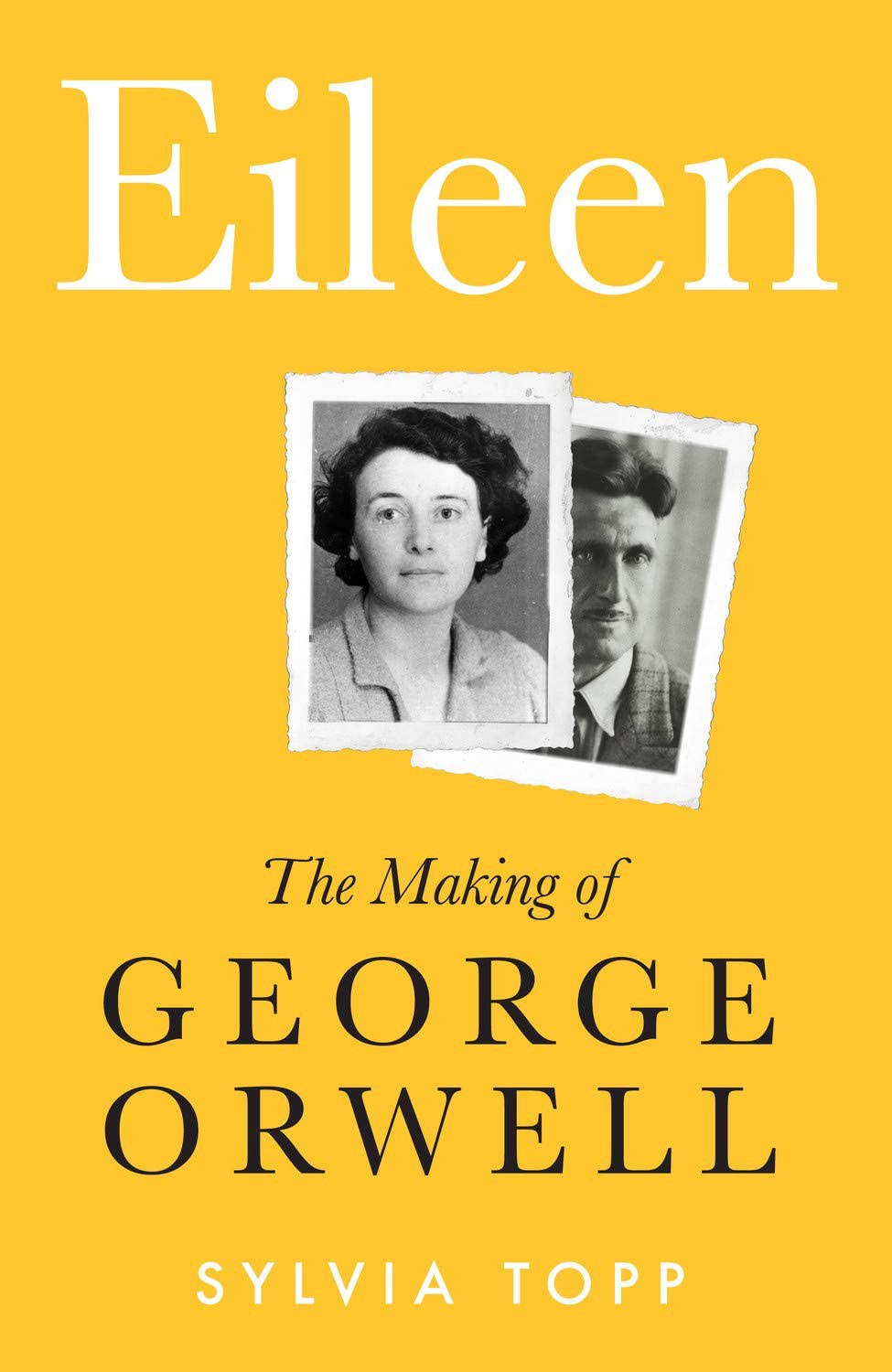我对共产党历史所知甚少,因此读这本书还是很受益的。我本来不知道 CCP 建立初期这么国际化。我也不知道赵紫阳、胡耀邦的改革倾向。虽然我知道胡耀邦的去世是学生抗议的开端,最后引向六四屠杀,但我对“胡耀邦倾向于改革”持怀疑态度,我的理念里共产党不可能有真的想要改革的人升职到中央,要改革也最多是经济改革,不可能民主政治改革。但是了解多了以后明白了可以认为当时有改革趋向。了解CCP的历史对我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更加了解了一些,我受到的教育,我被洗脑的内容,我至今的一些默认理解,都可以调整。
1920s
Tony Saich
Subject: Henk Sneevliet
这一章的文笔我不适应,读得很卡顿。后面的每一章还是比较聚焦被写的人物的,这一章则没有怎么刻画 Sneevliet。提到说他比较傲慢什么的,但说得很抽象。
主要是说他是 Comintern 派来的人。当时 CCP 刚刚成立(Sneevliet 有参加一大,他的中文名叫马林),Sneevliet 观察下来觉得应该和 KMT 合作,这就是统战 United Front。他似乎和孙中山更加相处得来,但是也有很多抱怨。大致是一开始 Comintern 方面赞同 S 的建议,但是中国方面不赞同。陈独秀和张国焘不同意。孙中山也不是很起劲。他的合作的具体建议是 CCP 成员加入 KMT,这个建议可能 CCP 和 KMT 也都不喜欢吧。后来呢,出现一些军事发展,还有俄国对 KMT 资助。这里有一个意识形态的确认,先把 KMT 定性为革命性的,所以可以资助。这时候陈独秀有点赞同统战了,孙中山接受了资助也好说话一些。张国焘很不同意,而且他和俄国有自己的渠道,Comintern 也开始反对了。
Sneevliet 后来被调离了中国,他的继任和他的看法相反。文中说他们两个人的交替也说明了俄国对中国的影响,从一开始的非常国际化的 Comintern 出发点转变为俄国国家利益的出发点。另外一种粗暴的理解也是托洛斯基和斯大林的区别。
我现在把共产党和民族主义等同起来,“马克思不是西方人吗”是个网络段子,没怎么想过 CCP 初期和国际共产的关系。同时,我是不是还或多或少地接受了 CCP 的 “别国内政” 说法,而其实,CCP 自己的源头也是一种国际思潮。只不过很快这种思潮就变成了民族主义,Comintern 变成了苏俄。
1930s
Hans van de Ven
Subject: Wang Ming
这一章的文笔好多了。王明(wiki 上显示他本名叫“陈绍禹”,没仔细看为什么换这么普通的名字)是。。这篇文章开头他就是 Comintern 派来的,到达的时候毛泽东去接机。这时候的主题还是统战,而且谈得非常好了,蒋介石和毛泽东在武汉……有一周的宣传周,大家都觉得要联合抗日了。然后是放弃防守武汉。长征以后 CCP 的军力大减,来到延安。(记得在 Coalition of the Weak 里看到这里毛泽东耍伎俩已经把 CCP 最精锐的张国焘的部队干掉了。)CCP 的军力很弱,所以似乎利好统战。但是毛泽东又一次说一套做一套,而且 KMT 自己也不是很强,所以合作不成。认真提合作的人必须处理一下,这里很可能王明被下毒了。然后他就淡出历史了。
1940s
Timothy Cheek
Subject: Wang Shiwei
王实味是投奔延安CCP的大批有志青年之一。他的才能是文艺方面的,他翻译了外国小说、马克思主义著作。在延安的时候,毛泽东号召文艺工作者出来做宣传工作。没想到得到的不仅是宣传共产主义,还有认真批评中央领导的。一起认真批评的别的人,很多都就范了,比如丁玲。王实味则比较理想主义,没有屈服。他还写了《野百合花》来讽刺毛泽东,登在《解放日报》上。毛泽东的策略是,出来说,是的我因为上大学所以沾染了一些资产阶级毛病,但是现在我觉得脚上有牛粪的农民最干净。王实味不就范,就只能抓起来。后来在一次军事转移的时候,可能拖着看押罪犯太累赘,就把他处决了。
这个时期毛泽东做的事情,提到什么延安文艺工作者讲话什么的,我以前也听说过。没有进一步了解过背后血淋淋的事实。
1950s
Zhang Jishun
Subject: Shangguan Yunzhu
上官云珠,来到上海工作后,有机会成了电影明星(上官云珠是艺名)。解放后,CCP 掌管所有的文艺工作,她这样的电影明星沾有资产阶级的污点。但是她非常积极,主动承认(并没有的)错误,非常配合(我觉得也许这是好演员的特质,非常配合表演,而且是深入意识里之后的表演)。她得到毛泽东的接见,所以同事领导都对她刮目相看了。(毛泽东可能就是喜欢美丽的女人所以接见了她。)她不再被打击,而是“可以被教育”的落后分子。她也拥抱这个标签。她演了一些成功的红色电影,包括一个电影是在海南岛上,她演一个行军护士,帮助她的伤员和大部队汇合。
虽然她被毛泽东接见了好几次,她还是逃不过文革。此时她已经被诊断了癌症,扩散到脑部,有时候无法说话。秦怡说她试图复健的时候认真学怎么说“毛主席”,两眼含泪。但是文革里她被打击,加上病情,最后自杀了。(自杀年份是1968年,想到前一阵一个帖子说中国版本的奥本海默怎么拍,有一个回复说,可以叫1968,然后列了一堆各种高学历的死于1968年的中国科学家。)
这一篇很明显是翻译的。我可以想象背后是有点空洞的中文。很多中文会习惯说一些空话。写作是困难的事情,再好的意图可能最后还是会借助一些空话度过难关。中文环境里很难不受影响。
1960s
Elizabeth J. Perry
Subject: Wang Guangmei
王光美,出身于北京的富裕人家,上大学,是中国最早获得核物理学位的女人(当时全世界也没几个吧?),会多国语言,有美国名校的录取。但是她决定为 CCP 工作,一开始做一些通讯翻译的工作。后来和刘少奇结婚(刘比她大二十几岁,她是第五任妻子)。她随同他参加一些工作,但是离开北京附近她就听不懂方言(尽管她会英语等三门外语)。五十年代刘少奇建议她去“蹲点”工作,她选择了河北的一个地方,这样她可以听懂方言。这就是桃园。她在这里工作了一年,本意是听取群众意见,整顿基层干部。群众发现整顿干部和地主富农后,大家可以瓜分财产,就都很起劲。这个经历向中央汇报,成了怎样发动运动的模版:要找到可以煽动的群众,要怎样发动他们,最后还要控制火候不要过分。(这套做法现在还在用,比如前一阵官媒宣传日本核废水排放,这几天开始说不要宣传了。之前钓鱼岛事件的时候,群众被煽动出来砸日本车,后续也是一个官方冷却的操作。)
没想到这个模版用在了文革上,王光美成了被整顿的对象。虽然毛和周都有保护刘和王,但是小将们采取了欺骗的方式,谎称他们的女儿受伤了,把他们骗到医院,当场捉拿。用极其羞辱的方式批斗他们。刘少奇后来死在狱中,似乎是死了好几天才被发现的。王光美被关押到文革后。出狱后她为丈夫平反,还设立了“幸福工程”的慈善机构。
前几天和朋友讨论,我去看了 Thomas Jefferson 的纪录片。片中说他的 contradiction :他写下了人类关于平权的最有影响力的文字,但他还是奴隶主。我觉得 Jefferson 的矛盾太容易理解了,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,把自己的 privilege 看作是应得的权利,而看不见自己压迫别人。而王光美的矛盾则更有趣不是吗?她设计了批斗的流程,然后自己成了被批斗的对象。
在桃园的时候,她让批斗进行得过头了?如果有腐败就应该实事求是,她有没有为了邀功而纵容?另外一个关键的因素我觉得是,我们没有一种原则。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,我以前为自己从小被洗脑崇拜毛主席而感到羞愧,而现在感觉更可怕的是,我小时候没有学到怎么做人。毛泽东看起来是个狡猾、心狠手辣、没有原则的人,说一套做一套的时候根本影响不了他说起来振振有词。而人应该诚实、诚恳、有良心、有原则、谦虚。这些标准,我似乎是成年后慢慢习得的。比起“爱国”洗脑,我现在更自怜自己在做人方面,输在起跑线二十年。如果我们有一种 judicial 原则,能在关键时候判断出“虽然共产主义理想是好的,但是这些官员没有做这些腐败”之类的决定,也许就不会有文革。问题是这些原则现在也没有。
1970s
Julia Lovell
Abimael Reinos Buzmán
这一篇我看得一愣一愣的。我本来就有一个疑问,为什么共产主义国家都变成集权国家了?现在对此我脑子里有一点点答案,这个答案来自 Marxist-Leninist 这个用词。列宁的成功的俄国革命给全世界的共产党强加了专制的属性,走和别的政党共存的民主路线,看起来就是错误的。改良主义帮助不了无产阶级!Maoists,我本来以为是不了解中国的欧美人赶时髦形成的。没想到 Maoism 往亚非拉输出其实很成功(因为 global south 的 institution 没有形成?)。这个秘鲁的追随者,学习毛泽东的理念和策略。他的革命没有成功夺权,但是做了很多残忍恐怖的事情。所以 Maoism 的精髓是什么呢?是“枪杆子出政权”,是“农村包围城市”,是策动群众。我想到我小时候翻家里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,觉得天文学、自然学的书扉页上都有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感觉很怪,我脑子里归为是那个时候的怪人怪事,以后不会有的,不理解很正常,是一种以前人的类似迷信的做法。也许某种角度看来,我就是一个需要被策动的群众,而且是个比较迟钝的那种。那么 Maoism 的表象是什么呢?我在这篇里看到了残忍。
1980s
Klaus Mühlhahn
Subject: Zhao Ziyang
赵紫阳,1919年出生,很早加入共青团,然后加入共产党。49年以后推进土改方面做得不错,调任广东省。他积极推进大跃进,然后发现行不通,所以政策略灵活。但是对上他比较服从,发表了一篇略质疑的文章后,就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样子。文革时他也被打倒,调到五七干校。但是他的日子没有太难过。邓小平上台后,把他调回广东。他试点农户家庭责任制,放开价格管控,在改革方面做得很成功,于是把他调到四川抓农村改革,然后升级到中央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,正式委员,总理,最后接替胡耀邦成为总书记。文中说胡耀邦是 intellectual,改革的信念出于理论,比较坚定。赵紫阳一直是实干家,改革的理念出自实践。这样看来他比胡耀邦温和。改革开放的很多基础是他先实践出来,打下的基础。他的市场经济改革完全不是出于什么理论,不是来自什么人权啊市场啊等等观念,而是来自实践,比如放开管控后,产量增加了。他发表的文章里的一句“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,被邓小平看中后成了党的slogan。As much as I hate slogans, as much as I dispute empiricism, I feel nostalgia for slogans such as this.
更难得的是,赵紫阳反对六四镇压屠杀和平抗议的人。因此他被撤职然后软禁到2005年去世。书上说,他没有写检讨。这一点也感觉很特别,也许现在不会有了,当时的共产党比现在的宽容一些。
书的最后说,赵紫阳和胡耀邦显示,改革的思潮一直存在于党内。共产党应该考虑一下。我本来想说作为共产党教育下的我本来完全不知道这些,说明共产党不想考虑这些。但是也许党校什么的对此有研究?书里这么说一句又略给我感觉是有讨好 bully 的嫌疑。
1990s
Xu Jilin
Subject: Wang Yuanhua
这一篇看了一半实在受不了跳过了。开头第一句里就有“法租界”,我的雷达就响了。没有见过无来由提这个词的文章是值得一读的。继续看下去,里面说 “虽然王元化自己不是基督徒,但是他基督徒家庭出身的背景让他不会盲从”,我无法表达我对这种说法的厌恶,你已经不是基督徒了,如果你还觉得基督徒信仰才能让人不盲从,那就等于承认你没有独立的智力。我觉得文章里对他的文革经历写得躲躲闪闪的,说1950s他不conform,后来坐牢,“坐牢的两年很shock”,然后就到了1980年代了。后面写到什么“南王北李”之类的,更是没有来头,只知道搬出这些语言来占好位置分个高低。听我说,党内知识分子反思文革,如果结局不是王实味那样的话,就说明没有反思。如果这个规律被打破了的话,请说一些实质内容。把苟且说成是反思,简直比作恶本身更恶心。虽然编辑已经说了读者可能会对这篇文章的文字感觉惊讶,我做了心理准备但还是看不下去,不逼自己了。
2000s
Jeremy Goldkorn
Subject: ?
这一篇打破了之前每一篇都聚焦一个对象的格式。不能说这一篇的 subject 是江泽民。可能是离现在比较近,要深入写一个这个时代的人物还不合适,人家还没死。之前所有的 subject 都已作古。很喜欢金玉米的文笔,带有一点点自谦的嘲讽正好足够。比如当时他在北京开的媒体公司还经过备案,还接受过官方 commission,他说“我当时真的认为我可以在北京开一家不经过审查的媒体公司”。作者对这一时期也是非常熟悉,列举了重要的事件。总结为 “得寸进尺” 非常合适:
The Party had given an inch in the “Three Represents,” but the society tried to take a mile.
而现在看这一时代,已经有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感觉了。我的重点不是诸葛亮,而是“事后”,这一时代已经过去。
2010s
Guobin Yang
Subject: Guo Meimei
这一篇的 subject 是郭美美,但也算不上聚焦于她,而是借她和一些别的例子讲网络管制的发展和手法。原来郭美美和中国红十字会的事情是2011年的,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。我也完全没有注意她入狱的消息,对她的指控和判罪有没有被舆情控制的需要影响?肯定是有的吧,有多少?也许很难研究,但是文中完全没有提,郭美美对这篇文章来说不是重点。这一篇从内容到说法我都很熟悉:CCP 发现网络舆论很厉害,从而加强了管制。但是我有一个想法,一直默认文字正常的人是这样想的,然而我好像没有怎么看到有人直说出来:对 CCP 官方解释的不满,主要是因为没有独立第三方检查,更深层的原因是 CCP 的权力没有制衡,没有另外一个政党,甚至内部没有三权分立之类的制约,这就没有让人信服的机会了。
当然,这是扯开了。这篇主要说一步步网络管制的措施,以及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情。